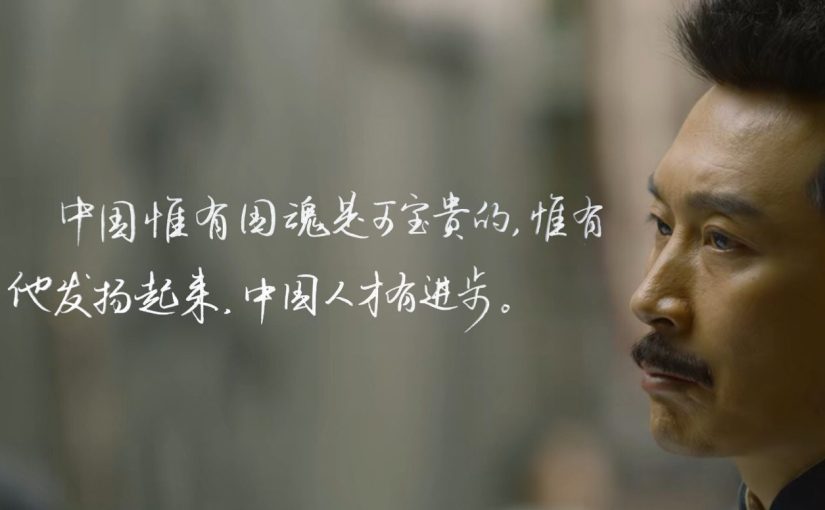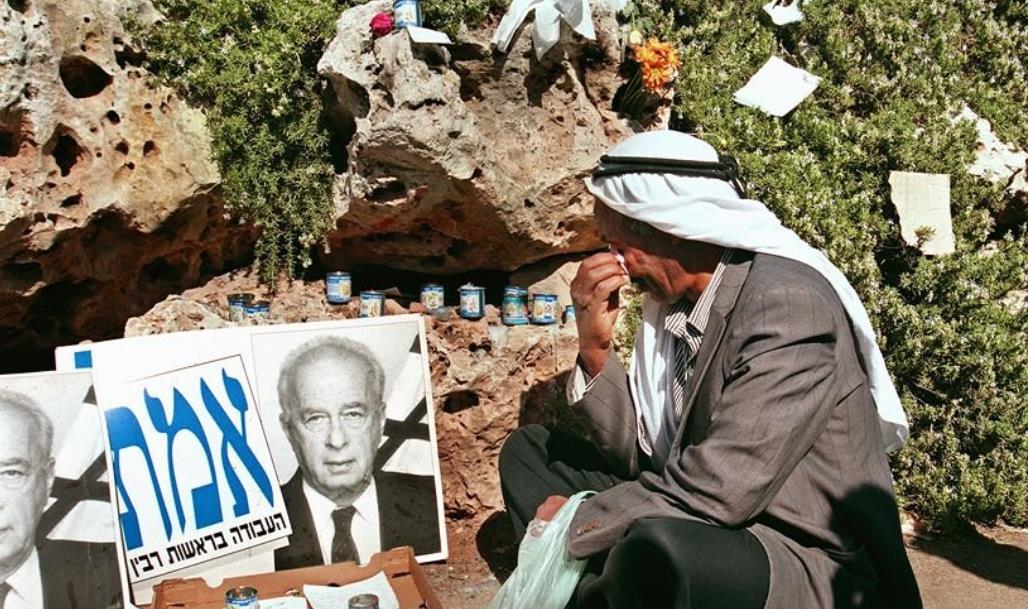根据中国房地产报的报道,简单总结如下:
“中国华融”变更公司名称为“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金融资产”。
原来的四大AMC
- 四家不良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中国长城、中国东方、中国信达。
- 依次与中国工、农、中、建四大行对应,一个行建立一个AMC。
- 创建原因是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用于处理中国银行业的严重的坏账(不良贷款率34%)。
- 财政部筹集资金1.39万亿元,由四大AMC转给银行,然后四大AMC接手处理不良资产。
- 由于在经济低迷期拿到的不良资产,有可能在经济复苏时爆发,四大AMC随后就迎来了黄金时代。
华融变更前
- 2016年华融净利润231.1亿元,总资产1.41万亿元,收入来源包括不良资产经营业务53%、金融服务业务25%,资产管理和投资业务22%。
- 2021年华融公告净亏损预计1029.03亿元。
- 2022年财政部将其持有的华融24.07亿股内资股向中信集团增资,中信集团持股比变为26.46%,成为华融第一大股东。
新三巨头传闻
- 据传闻,另外三家AMC——中国长城、中国东方、中国信达,将并入中投集团。
- 中投是国务院直管的“投资国家队”,注册资金1.5万亿元,总资产近10万亿元。
- 四大amc落幕后,中信、中投、中国银河将成为新三巨头。
中国银河从哪儿来的
- 2005年华夏证券破产一分为三:中信建投证券、建投中信资产管理和华夏证券。
- 中信建投证券:中信证券持股60%,建银投资持股40%,从华夏证券手中接过其证券业务。
- 建投中信:中信证券持股30%,建银投资持股70%,从华夏证券手中接过非证券类资产。
- 华夏证券保留空壳公司,承接债务。
- 2020年中国银保监会批复同意建投中信转型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更名为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中国银河定位于侧重处理证券、基金等金融类不良资产。
- 中国银河的最初持股结构为: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65%,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13.3%,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6%,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