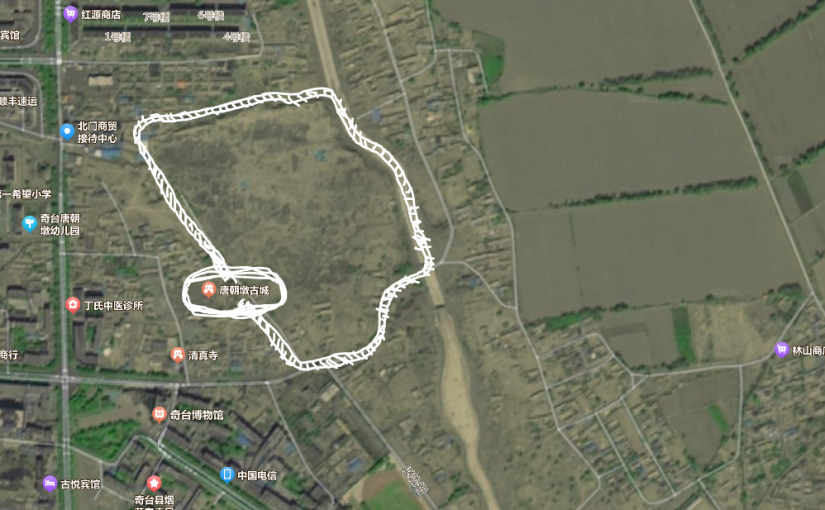乌克兰是除俄罗斯以外欧洲面积最大的国家,约60.37万平方公里(法55/德35.7),人口4100万。
首都基辅曾是超级大国“基辅罗斯”的中心,13世纪基辅罗斯被蒙古人灭掉后才逐渐演化出乌克兰、俄罗斯、白俄罗斯三大分支民族,相当于三大民族发祥地。
苏联时期,乌克兰在没有独立的情况下,获得了联合国的成员国席位。基辅是苏联第三大城市。乌克兰曾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包括核工业、航天工业、造船业、军工业、机械制造、化工业、冶金工业等等。
目前,乌克兰已经从一个工业发展水平可与法国和中国媲美的国家变成第三世界国家。
这是怎么做到的?
苏联解体后,激进的私有化和混乱的政治让乌克兰损失了高达60%的GDP,即使是处于战争中的非洲国家也没有这样的损失。上世纪90年代,乌克兰甚至没有战争。
不过,就算工业指望不上,乌克兰也还是有拿得出手的东西。
全球1/4的黑土地都位于乌克兰,真金饭碗。目前,乌克兰是世界第三大粮食出口国(第一大葵花油出口国、第三大玉米出口国、第四大小麦出口国),被称为“欧洲的粮仓”,中东对乌克兰小麦的依赖也已高到“危险的程度”。
2021年,乌克兰对中国出口最多(80亿美元,同比增长12.7%),其次是波兰(52.3亿美元)和土耳其(41.4亿美元)。主要出口商品是黑色金属(139.5亿美元)、谷物(123.4 亿美元)和动植物油脂(70.4亿美元)。自中国进口最多(109.7 亿美元),其次是德国(62.8 亿美元)和俄罗斯(60.8 亿美元)。主要进口矿物燃料、石油及其蒸馏产品(143.3亿美元)、机械设备(142亿美元)、化工及相关行业产品(97.4亿美元)。
明面看起来还不错,乌克兰的老百姓过得怎么样呢?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的2021年数据,乌克兰的人均GDP仅有约3984美元,在所有欧洲国家中位列倒数第一,甚至落后于很多非洲国家。
苏联时期,乌克兰有800多所的高等院校,人口受教育程度居世界前列,有职工为300万人的3594家军事工业企业,有世界著名的安东诺夫飞机设计局、研发坦克的哈尔科夫设计局、航母摇篮尼古拉耶夫造船厂、研发火箭和战略导弹的南方设计局。现如今,在乌克兰,教师、医生和有能力的专家都很短缺。
为什么?
寡头利益集团把持乌克兰经济,操弄乌克兰政治,所有的利润都被私有化,所有的损失都被国有化。腐败感知指数,乌克兰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17位,在欧洲排名倒数第二。
所以,乌兰的寡头很有钱,而且寡头都靠不住,卖国有他们,爱国没他份。
日前,约23名国会议员和约100名富豪紧急飞往国外。截至2月13日晚航班停运,包括乌克兰首富里纳特·阿克梅托夫在内的福布斯乌克兰百大富豪大部分离开,只剩4位留在国内。
寡头不愿出钱,谁来出?在寡头的操作下,乌克兰人民要向寡头们的精神祖国要饭吃,这饭还不白给,是要还的。
美国政府2月14日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主权信用担保的贷款方案。最近乌克兰还获得了英国、法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国的“财政支持”。
这就是捧着金碗要饭的乌克兰:金碗属于寡头,要来的饭由寡头吃大头;人民穷苦来自于寡头,这种穷苦又被寡头用来要饭;寡头连一丁点残羹冷炙都不愿让与人民。自治较好、亲俄的乌东部要造反,能怨谁呢?